There is no improving the future without disturbing the present.
– Catherine Booth
There is no improving the future without disturbing the present.
– Catherine Booth
保持快乐的秘诀,其实就是五个字:不要太用力。做事业不要急于求成,交朋友不要掏心掏肺,谈恋爱不要占有,过日子不要追求完美。获得什么便珍惜什么,失去什么便接受什么,给我的我欢喜,不给我的我不焦虑,就是这样,付七分力气留三分给嬉戏。
“他只是跳出了时间,变成宇宙里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分子、原子,慢慢的重新构建成你身边的其他事物。以后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是他,为你抵挡寒冷的毛衣是他,当你疲惫时看着桌头的挂件还是他,他是你亲人的身份消失了。但是其实他以后无处不在。他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稻盛和夫有一句特别牛逼的话,特别适合现在:
渔夫出海前并不知道鱼在哪里,可是他们还是选择出发,因为他们相信,一定会满载而归。
人生很多时候,是选择了才有机会,是相信了才有可能。 继续阅读“渔夫出海前并不知道鱼在哪里,可是他们还是选择出发,因为他们相信,一定会满载而归。”
希望大家知道的是,无论是谁,一旦受到超过承受上限的压力时都会变得暴躁、哭泣、具有攻击性、抑郁、甚至无法保持理智。人类是很脆弱的,一个人之所以能一直保持正常,是因为他处在正常的环境中,而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正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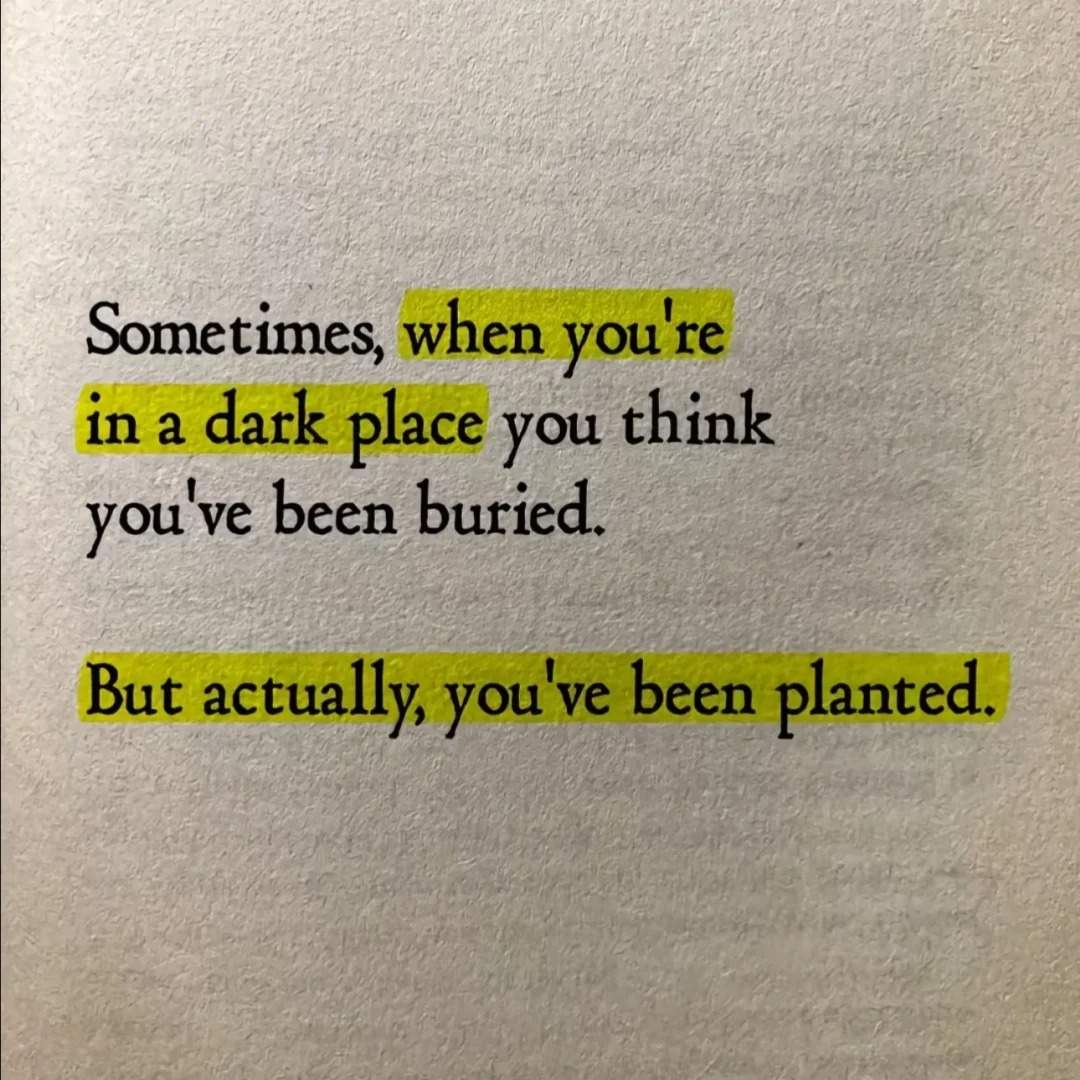
Sometimes, when you’re in a dark place you think you’ve been buried.
But actually, you’ve been planted.
Your friends’ problems become your problems.
The smaller your circle, the less bullshit you have to deal with.
People want you to succeed…
But not more than themselves.
别人希望你成功…… 但不希望你比他们更成功。
Whether it’s a machine, a house, or a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is always cheaper than repairing.
不管是机器、房子,还是处对象,平时多维护肯定比坏了再修要省钱。